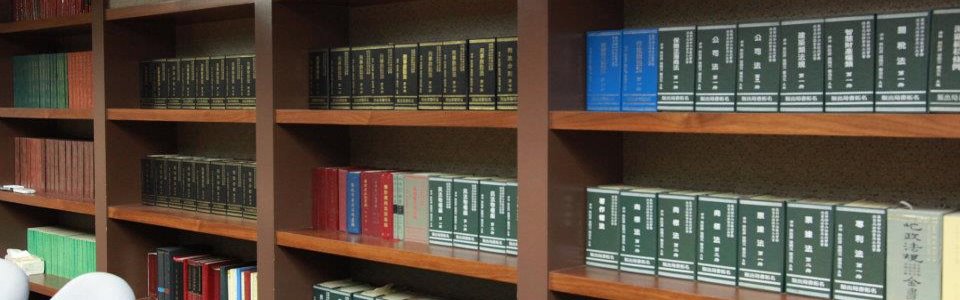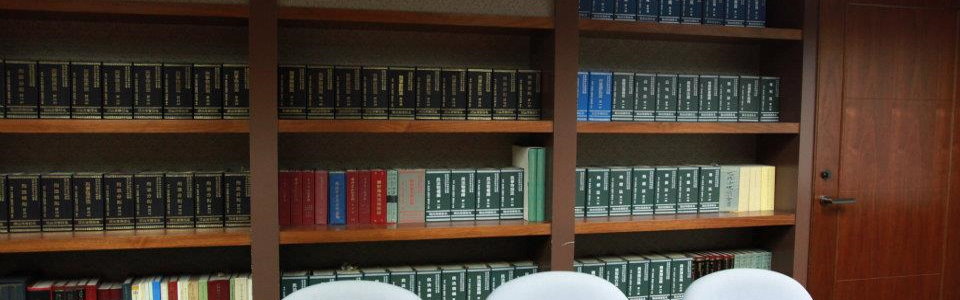知識快訊
憲政維持與權力僭越之界——從WTO上訴機構癱瘓談我國大法官人數不足的憲政困境
作者:李明諭 律師
憲法法庭的存在,象徵一國憲政體系的最後防線。當權力分立的三角結構因政治延宕或人事真空而失衡時,司法作為守憲者是否可以「自我解釋以維持秩序」?這一問題,在我國當前大法官人數僅剩八位、低於憲法訴訟法規定的十五位法定人數時,已不再是理論假設,而是具體現實。司法體系是否能在制度殘缺下繼續行使憲法審查權,成為憲法秩序延續與合法性維繫之間的矛盾焦點。
在憲法結構上,法定人數並非單純的行政門檻,而是機關合法性的構成要素。大法官的設計,不只是「足夠人數」的要求,更體現「多元合議」與「正當授權」的精神。若人數低於法定組成標準而仍作出解釋,其正當性基礎便立刻陷入懸空。法院若主張「因為憲法救濟權不可中斷,所以必須繼續審理」,此論雖情理可通,卻可能落入自我授權的陷阱。畢竟,司法權並非自生,而是憲法明文創設。倘若「守憲」成為違憲的理由,那麼,維護憲政秩序的法庭,反而可能成為違憲秩序的開端。
然而,若憲法法院全然停擺,人民的憲法救濟權亦將化為空文。於是,一種「憲法必要性原則」的論調出現——法院可以在極端情況下,以「維持憲政連續」為名,採取有限度的自救行為。此一理論並非無本可據。從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到印度最高法院,皆曾在國家緊急狀態中引用「doctrine of necessity」作為臨時運作的憲法例外基礎。然而,這一理論的危險正在於其模糊:一旦缺乏明確邊界,「例外」就可能被誤用為「常態」,從而破壞憲法自身的防衛機制。
在這裡,值得引入國際法的一面鏡子。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自2019年底陷入「法官不足」的癱瘓狀態,恰恰展示出制度在合法性危機下的另一種選擇。根據爭端解決規則(DSU)第17條,WTO上訴機構應有七名成員,每案需由三人組成審理小組。由於美國長期封鎖新任命程序,至2019年12月僅餘一名成員,無法依法組成審理組。這意味著所有上訴案件自此「進入虛無」,即 appeal into the void,制度功能陷入停擺。值得注意的是,WTO並未讓殘存成員以「自我延任」或「緊急審理」的名義繼續行使權力。成員國選擇的道路,是尋求臨時替代性制度——歐盟與十多個成員國建立的「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MPIA),正是在合法範圍內的制度性修補,而非內部機關自我膨脹的擴權行為。 WTO的選擇揭示了一個重要原則:當制度合法性遭侵蝕時,維持秩序的手段不能依賴單方機關的自我正當化,而應透過外部合意與程序重構來重建合法性。若司法機關因人數不足而繞開法定程序、以自解釋方式持續運作,雖可暫解功能危機,卻可能損及更深層的憲政信賴。人民信賴司法權的前提,是相信其權力源自憲法,而非自我創設的權能。
回望我國現況,憲法法庭若採「最低限度運作」模式,例如僅處理程序性事項、暫緩實體裁判,或許尚能在法理上找到立足點。此種作法並非全面擴權,而是基於憲政延續的自我節制。若要採取更進一步的「有限實體審理」,則必須附帶極嚴格的自我約束條件:僅於憲政運作將陷全面中斷時啟動,且須明確公告期限、範圍與補正機制。更重要的是,應在新任命完成後由完整組成之大法官會議重新審視該期間的裁定效力,以免形成永久性的權力偏移。
理論上,這種「必要性自救」之所以能被容忍,是因為它自覺地保持「過渡性」。一如醫生在緊急手術中使用未經核准的藥物,目的是爭取時間,而非改變醫學規範本身。若法院以「憲法維持」為名進行制度性創設,那就不再是救治,而是重寫憲法。這種「以守憲之名行制憲之實」的行為,會讓司法獨立演變為司法霸權。
因此,真正的解方不在於司法自救,而在於制度補強。立法機關應建立明確的補位機制與時限,防止任命懸缺成為政治博弈的工具。同時,憲法訴訟法亦可增設「臨時法官制度」或「代理審理制度」,以確保即使部分出缺,仍能維持法定運作門檻。此外,制度透明化亦至關重要。任何憲法法庭在例外情況下採取的運作措施,都應有公開說明、外部監督與事後檢視,否則「必要性」終將成為權力的護符。
從宏觀的憲政哲學來看,司法權的真正力量來自自限,而非擴張。正如WTO的選擇所示,一個有自知的制度寧願暫時沉默,也不願僭越規範說話。沉默是一種尊嚴,而僭越則可能是體制信任的終結。台灣的憲法法院若要在困境中維持公信,就必須在「憲政連續」與「權力合法性」之間找到那條細微的平衡線。
守憲不只是維護條文的存在,更在於維護憲法運作的正當形式。若形式被破壞,憲法的精神也隨之動搖。大法官可以為了憲法延續而點亮微光,但不該為了權力延續而燃起自己的影子。這是WTO案例教給我們的憲政倫理,也是台灣法治社會此刻最需警醒的課題。
2025/10/13

事務所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04號7樓
E-MAIL:chinyuilaw@gmail.com
聯絡電話:(02)2396-8399
免費諮詢:(02)2396-2224
傳真電話:(02)2396-8398
政諭法律事務所 版權所有c2019 CHIN YUI ATTORNEYS-AT-LAW.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