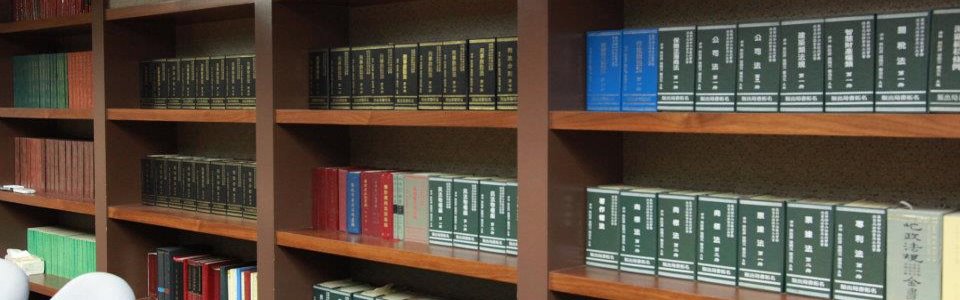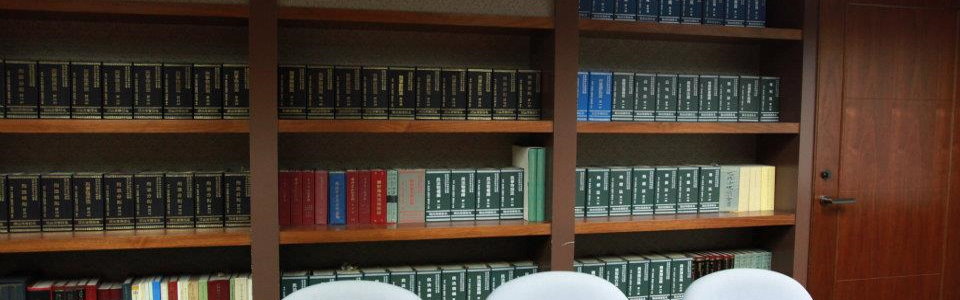最新消息
連錯話都不能講的社會,才最可怕——從王男案看言論自由的真諦
作者:李明諭 律師(政諭法律事務所)
壹、警方眼中的「謠言」,其實只是你不喜歡聽的話
王男在臉書上寫了兩句:
「國民黨喊普發一萬就沒看過你們下標題,這是假訊息」;
「梗圖早上一出,婆婆媽媽公公四處信以為真,蔣萬安跟盧秀燕也是馬上回應,半天翻一次頁、這麼好用還不用」。
台中警方震怒,認為這是「未經查證的內容」,恐「影響公共安寧」,於是隆重地移送地檢署。
在警方的三觀裡,「公共安寧」不再指社會秩序,而是當權者的安寧。
批評政策、嘲諷政治人物、玩個梗圖,都是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
民主的奇景就是:
一張梗圖能動搖國本,一句玩笑能破壞秩序。
要不是法院還記得憲法,我們大概離「笑話審查法」施行,就只差一紙行政命令。
貳、法院的回答:刑法不是思想編輯器
法院這次非常清醒:
「散布謠言」要構成犯罪,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
一、明知內容不實;
二、故意散布;
三、足以引起恐慌。
三缺一,就不成罪。
王男不過是對普發現金政策發表辛辣意見,這在民主社會是日常呼吸。
法院引用憲法第11條與釋字第509號、第744號指出:
涉及公共事務的言論,即便偏激、諷刺或荒謬,也屬憲法核心保障。除非造成「明確且立即危險」,否則國家不得以刑罰干預。
翻成白話:政府沒有資格管人民講話難聽。
但在台灣,這一般常識的句子,聽起來仍像叛逆宣言,尤其有些人還活在封建的父權社會裡,更是覺得大逆不道。
參、大法庭的立場:民主要能容忍「錯的言論」
最高法院大法庭刑總第14號決議明確指出:
「僅有明知虛構且足以引發恐慌的謠言,始得處罰。單純意見表達,不得援引刑法第149條。」
這句話不是溫柔提醒,而是對濫權偵辦的警鐘。
公權力最喜歡說:「我不是要你閉嘴,只是請你查證。」
但你仔細想,這不就等於「沒拿出證據就不准講話」?
那公民社會就會變成新聞部審查局,人人發文要附註腳,連開玩笑都得先驗證。
言論自由不是「只能說對的話」,而是「即使說錯,也不該被抓」。
🤔 錯誤的言論是辯論的燃料;荒謬的想法是思想的礦石。(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1859)
密爾在論自由第三章說得最接近這個意思:
“The peculiar evil of silencing the expression of an opinion is, that it is robbing the human race... If the opinion is right,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error for truth: if wrong, they lose, what is almost as great a benefit, the clearer perception and livelier impression of truth, produced by its collision with error.”
(譯:壓制意見的最大罪惡,在於剝奪了人類的真理機會。若該意見正確,我們失去修正錯誤的機會;若錯誤,我們也失去真理在衝撞中更清晰的光芒。)
→ 這正是「錯誤言論是辯論燃料」的哲學來源。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Abrams v. United States, 250 U.S. 616 (1919) 的反對意見中寫道:
“The best test of truth is the power of the thought to get itself accept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the market.”
(譯:真理最好的檢驗,是它能否在思想市場的競爭中勝出。)
→ Holmes 的這句話啟發了「Marketplace of Ideas(思想市場)」理論。錯誤的思想正是市場中的燃料,沒有競爭,就沒有真理的鍛鍊。
Justice Louis Brandeis, concurring in Whitney v. California, 274 U.S. 357 (1927)
Brandeis 強調:「公共討論是民主的最大保障,唯一可以對抗錯誤言論的方式,就是更多言論。」
If there be time to expose through discussion the falsehood and fallacies... the remedy to be applied is more speech, not enforced silence.)
若國家用刑罰提煉真理,那民主只剩鐵鏽味。
肆、言論自由的真諦:讓人可以講廢話,也可以講真話
大法官講了三十年,人民卻還得靠法院提醒:
言論自由不是讓你愛國,而是讓你有權不愛。
不是讓你說「對的事」,而是保護你說「不對的話」。
警方若覺得貼文有誤,該做的是公開更正、展開辯論、說服人民;
而不是先上銬、再說「我們尊重言論自由」。
這種邏輯,就像拿刀割人,然後說自己是外科醫師。
伍、延伸分析:法院的界線與大法庭的警語
刑總第21號大法庭決議(111年12月22日)再度確認:
「對涉及公共事務之意見表達,應以最嚴格標準檢視刑罰介入之必要性。」
「意見表達若僅具爭議或誇飾性,尚難認對公共秩序產生具體危險。」
這是台灣司法少見的清醒語言。
法院要求國家「舉證危險」,而不是人民「證明清白」。
這個觀念,正是民主與威權的分水嶺。
以前是人民講話被查水表;現在,法院要政府證明「水真的會淹出來」。
這才叫文明。
陸、比較法觀點:民主的底線在於容忍
這種思維並非台灣特例,而是現代憲政共同語言。
1.美國法的源流——Brandenburg v. Ohio, 395 U.S. 444 (1969)
美國最高法院指出:
「除非言論意在煽動、且極可能立即引發違法行為,否則不得以刑罰限制。」
這就是所謂的「明確且立即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則。
王男的貼文離「煽動暴亂」還差幾個宇宙。
2.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Lüth 判決(1958年)
判決明言:
「言論自由是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根基;民主社會的力量來自討論,而非服從。」
Lüth 案至今仍是歐陸法制的座標。
若德國能容忍對政府的尖銳批評,台灣卻容不下一張梗圖,那叫進步嗎?
3.歐洲人權法院(ECHR)Handyside v. UK, 1976
歐洲法院直白地說:
「言論自由不僅保障被認為無害或無關痛癢的言論,亦保障那些冒犯、震驚或使人不安的言論。」
因為那正是「多元與包容社會」的核心。
在國際人權法(ICCPR第19條)下,表達自由的限制必須符合三原則:合法性、必要性、比例性。
王男案的警方移送,三者全無。
要說「公共危險」,恐怕真正危險的,是那雙隨時準備封嘴的公權力。
柒、結語:最可怕的不是假消息,而是怕消息
王男案看似小事,其實是民主呼吸的測試。
法院守住了界線,提醒我們——法律不是壓制思想的工具,而是思想得以生存的空氣。
我們可以討厭王男的話、笑他嘴賤、罵他偏頗;但只要這個社會還能讓他講——這才叫民主。
真正的公共危險,不在那一則貼文,
而在那雙太急著讓人民閉嘴的手。
伏爾泰: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原文: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參考法源與判例
中華民國刑法第149條、第153條
司法院釋字第509號、第644號、第744號
最高法院大法庭刑總第14號決議(2021.10.28)
最高法院大法庭刑總第21號決議(2022.12.22)
Brandenburg v. Ohio, 395 U.S. 444 (U.S. Supreme Court, 1969)
Lüth Case, BVerfGE 7, 198 (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 1958)
Handyside v.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5493/72 (ECHR, 1976)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19條拿
Facebook 留言點讚
遇到法律疑問嗎?不用煩惱,直接來電本所,專業團隊隨時為您解答。
📌 本文由政諭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李明諭律師 審訂
📌 若需引用,請註明出處「政諭法律事務所」並附上本文連結
2025/11/8

事務所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04號7樓
E-MAIL:chinyuilaw@gmail.com
聯絡電話:(02)2396-8399
免費諮詢:(02)2396-2224
傳真電話:(02)2396-8398
政諭法律事務所 版權所有c2019 CHIN YUI ATTORNEYS-AT-LAW. All Rights Reserved